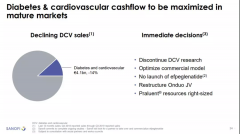|
在过去的一年里,故事写作营陪伴了近千位写作者,从踽踽独行到结伴组队,在写作营里完成一次次的写作练习,通过视频、直播课程更进一步了解写作,一起读经典,一起讨论创作,一起在限时写作的压力下,完成属于自己的作品。 如今,故事写作营已经到了第五期。我们坚信,写作需要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同样,写作也离不开好的导师和同行的伙伴。
细讲的话,写作的幸福是输出的时刻,感觉自己在制造某种晶莹剔透的东西。一个句子或一个想法,被方块形状的字固定凝结,这个形状像火一样烧着我的心使我落泪。 比如我现在在黑暗中写作,可我的眼睛被屏幕上的字吸引了,黑暗又浓又重却离我远去了。如果在文字中宣泄或是赞叹,那一份剥离出血肉的情感就像新生的婴儿在我眼前跳动哭泣。就好像你在用文字繁衍,生命短暂且世事无常,只有这一刻是沉寂温柔的,可以静静地、默默地写,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联系上爱与死与美,那个时刻仿佛与伟大短暂相连。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虚构写作一些,如果能把脑内的光怪陆离形成有节奏的诗意语言就会觉得是莫大的幸福,追根究底,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只是想让自己的脑子停止不安的躁动,变成一只温驯的野兽。 痛苦是写作仿佛在自残。每个字都从皮肤上脱落,可每个字我都不喜欢,它们的排列方式、语音语调,我总觉得应该是有更好的,不满足,甚至为这些出自我手的文字而感到万分羞愧。因为读书,就见过天才般的文字是多么热烈且富有欲念以至于顽强的扎根在人的心中。 读一口诗、一段话、一句天籁的词。因为见过耀眼的太阳就被致盲了似的,伊卡洛斯的结局是永远的坠落。所以对自己苦恨、失望,于是恐惧,不敢去落笔了。我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爱写作又这样恨它,爱和恨竟可以这样彼此遮掩相连。 之所以参加“故事写作营”也是想借由外力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这块顽石堵的我苦不堪言。十七八的时候语言像涌向大海的洪流无止境地外泄,也许是竭泽了,现在的我仿佛丧失了写作的能力。我不明白自己的恐惧从何而来,但希望能消解它,让我重新捡起写作,找回遣词造句的能力,像母亲拾回因战乱而失去的孩子。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折磨我很久了。所以选择在深夜动笔,用被子裹起自己制造一种过期的安全感……即使每个字都好像伤疤一样赤裸的展现在大家面前。又怕这样的伤疤引起各位的嗤笑,因为伤口即使愈合留下的痕迹终究是不讨喜而丑陋的,而人们总是尚美、纯洁和高贵才是。 如果不是因为心中困兽,写作和自己没啥关系。如同剥洋葱,一层层盘剥下来,淋漓尽致,全部的我跟镜子一样立然眼前,所有的较劲,狰狞,爱做梦的样子,一丝不挂跟那杵着,不那么好看,贵在看见,看见于是松动,于是对自己渐生爱怜,渐生爱意,于是镜子那头另一面的自己一样独独在跟前立着,安静又笃定,友善里赋隽永的爱意。 这样的我,那样的我,他们都根根分明地立着,在那头的世界里,交错间,仿佛完成了某种仪式,何为“我”。 总感觉在写同一样东西,读书的时候就抱怨又在说这东西。我写的那些东西里的人物、背景、情节都不同,但表达的东西相差无几。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被我反复表达的东西我没能力说清,我只能意识到那和人类的处境有点关系。就因为这样,我写作的时候总觉得没新意,看书的时候总觉得在看同一本书。 高中以后走了理工的路子,基本没有再提笔创作。但会把写作作为分析问题的工具,生活工作中遇到想不清的问题,会用笔思考,一来条理清晰,二来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坦诚自己是个功利的写作者。曾经,我爱写作,是因为老师会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在全班面前朗读,我很享受那种被人瞩目的感觉;读大学时,加入文学社,发表一些小豆腐块,大家戏称我为“才女”。这些小小的荣誉,带给我大大的虚荣和成功的喜悦。 |
热门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