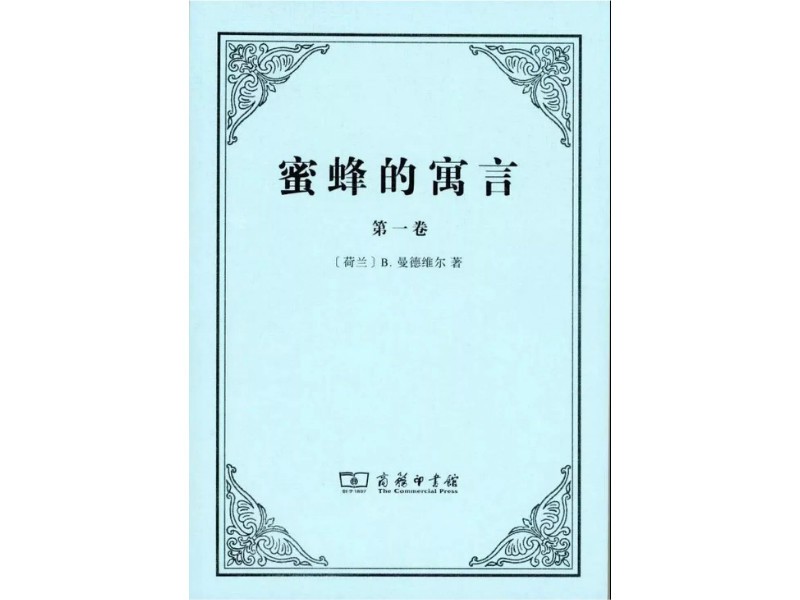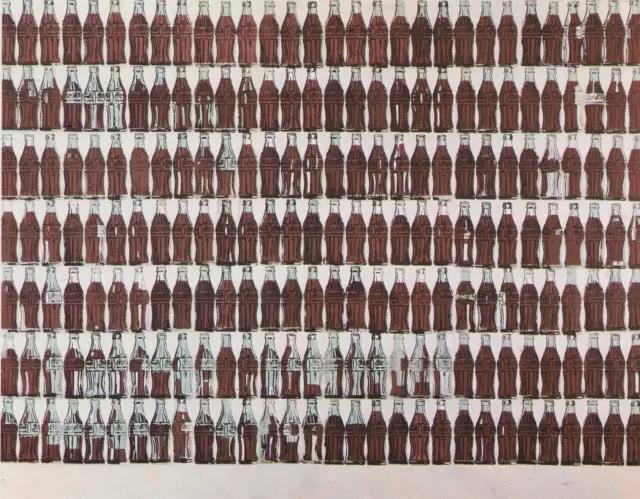|
1998年修订的《新华词典》中有这么一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现在这句话变成了网络热梗,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事实就是如此。售货员属于最好的工作之一,处于全社会的前15%高端群体。他们知悉物资供应的内部信息,直接参与财富的分配,《平凡的世界》里面,红梅的父亲千方百计把她送进供销社当售货员。由于货物短缺,人们哄抢,时常有恶性事件发生,百货商店给售货员的员工守则里特意标明:“禁止殴打顾客”。
那消费主义又是如何兴起的呢?古今中外,无论是中国的儒家社会,还是西方中世纪,大部分时代以提倡勤俭节约为主流,鼓励享乐消费的是异类。 18世纪曼德维尔写作《蜜蜂的寓言》时,首次公开提出奢侈有益于经济,“节约是个人的美德,却使社会萧条;浪费是个人的恶行,却使社会繁荣”。结果社会各界一致谴责曼德维尔,连自由放任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都斥责他大逆不道、完全有害。 东亚发生了类似的争议,明代中后期市民经济繁荣后,一些官员主张打击奢侈风气。湛若水担任南京兵部尚书期间,禁止百姓从聚饮酒、游嬉。万历年间江南大荒,苏州官员主张禁止游船等奢侈消费。在当局看来,旅游是不务正业,破坏大明社会风气。 幸好还存在富有经济头脑的人,当过布政使的学者谢肇淛指出,国家兴亡与游人、歌妓无关。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反而显示出太平气象。江南有个县的地方志支持谢肇淛的观点,奢侈不足以使天下贫穷,而节俭至多让一人一家得益。作者举例,当时消费主义文化越是浓厚的县镇,民众谋生越是容易。 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能认识到享乐主义对经济的正面作用,在三四百年前却是异端邪说。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 更进一步,认为消费不仅有益产业发展,而且促进了民主化。消费尤其是服装领域的消费,让美国人有别于欧洲。在欧洲城市散步,你从一个人的衣着打扮,就能看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平民贵族的衣服都有严格的等级分层,在美国你很难分辨得出。
匈牙利的政治家弗朗西斯·普尔斯基1852年在美国旅行,他感慨美国人穿得都一样。在本国,德高望重的老妇人和未婚女子穿得不一样,地主和农民穿得不一样,匈牙利农民和斯洛伐克农民穿得还是不一样。 南北战争前,英国人托马斯·科莱奇·格拉顿担任驻波士顿的领事,他发现美国的仆人穿得很考究,自己从英国带来的女仆也受风气影响,效仿起来。英国商人W·E·巴克斯对这种现象愤愤不平,说美国工人的打扮和职业不相称,逾越了身份等级。他说:“普通工人干的是最脏的工作,却穿着华丽发光的黑色衣服……这里的老百姓应该懂得,衣着的选择应当实用而不是为了炫耀。” 19世纪莎夫茨伯里七世伯爵,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消费场所必须在星期日关闭,这一天用来上教堂。伦敦工人阶级非常恼火,因为贵族不上班,随时都可以购物,而工人只有星期日一天能放松休息。 美国市民消费文化异常发达,商家率先创造了百货公司的经营模式。此前西方的集市上,摊贩把真正的好货藏起来,陈列在外面的都是普通商品。在家具服装等行业,店铺挂出某一家贵族的家徽,表明自己是这家贵族的制定供应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派头。顾客要买上等货,必须经圈内人介绍,才能入店。
|
热门关键词: